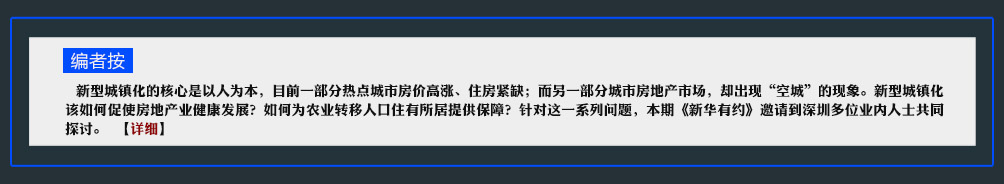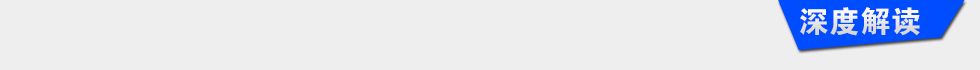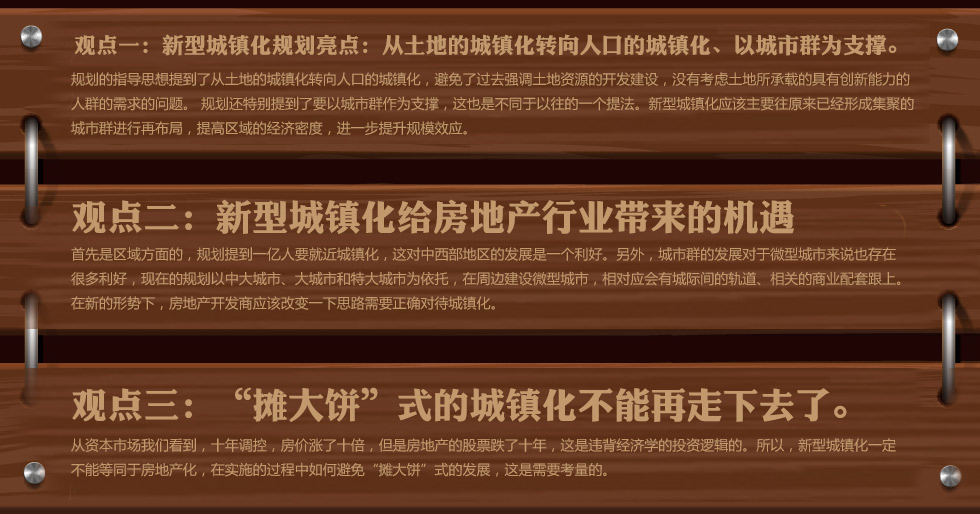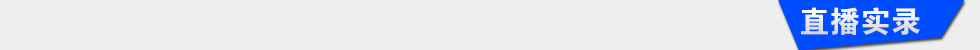|
主持人: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以人為本,隨著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的持續推進,無論是從農村到城市的轉移,還是不同城市間的轉移,都必然擴大對住房這種基本生活資料的需求規模。同時,新增城市人口的住房需求也必然會對房地產市場格局帶來新的變化。新型城鎮化將對樓市產生哪些影響?
首先介紹一下今天出席的嘉賓: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區域發展規劃研究所副所長劉國宏、中原地產研究中心經理王飛、中銀國際證券有限責任公司黃海勇。
新型城鎮化是從去年十八大到今年兩會期間,各界關注的熱點話題。我們注意到,十八大報告中有兩個熱詞格外引人關注,一個是“美麗中國”,一個是“城鎮化”。這兩個詞有何內在關聯?城鎮化和城市化有什么區別? 在座的各位怎樣解讀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城鎮化”建設?
綜合開發研究院劉國宏:十八大報告里提到兩個關鍵詞,一個是美麗中國,一個是新型城鎮化。
首先,美麗中國和新型城鎮化的內在聯系是城鎮化是實現美麗中國的重要手段。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后,在新的時間節點上,我們提出要打造美麗中國,也就是說生態、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都要有較大改善和提高。
而城鎮化本身不僅是一種經濟的集約利用,資源的優化配置,同時也是處理一些生態問題、社會問題,提高人民文化修養、文化水平的必要手段,因此我認為這兩個詞有非常緊密的聯系,城鎮化是實現美麗中國的核心手段。
第二,大家都在提城市化、城鎮化有什么區別,事實上這兩個中文詞在英文里是一個單詞。在中央的文件里使用的是城鎮化,通常老百姓的理解是大、中、小規模的城市,而成規模、成建制的鎮也是城市的一種形態,所以其實沒有必要非得追究這兩個詞的區別。
最后,十八大報告里提到城鎮化部分有一個主題就是科學發展,主線就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依靠什么?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轉那些?
如三架馬車的結構,投資、消費、出口。首先一定要改變投資驅動發展的方式,因為這個方式帶來了很多弊端。而在出口方面,國際市場也不景氣,那么能依靠的就是消費,其中,擴大內需是我們十八大的重要戰略,而城鎮化正是我們擴大內需的重要手段。
從我們產業結構的轉型看,我們城鎮化的建設既給我們的產業提供了市場空間,也給我們的產業提供了新的載體,所以一些沿海城市的產業往哪轉移,城鎮化建設就是告訴這些產業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還有很多地方適合這些產業的發展。
此外從文化上,生態上,人口的積聚才能帶來交流、溝通,才有可能帶來我們文化水平的提高,甚至帶來我們的政治文明。以希臘為例,希臘是西方世界早起政治最文明的地方,而這些就是城鎮建設和城邦間的博弈帶來的。
也因此,這次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城鎮化,對我們的下一個三十年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中原地產王飛:首先,美麗中國和城鎮化的關聯還是要回到新型城鎮化和舊城鎮化的區別上才能體現出這兩點的關聯。舊城鎮化是以犧牲環境資源為代價,新型城鎮化是以生態建設為基礎,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所以新型城鎮化和美麗中國是相互促進的關系。
其次,城鎮化和城市化我們追溯國外的一些歷史可以發現這兩者沒有什么區別。而此次城鎮化的落腳點是落在城鎮上,城鎮化的主體、城鎮化的人口都更加偏向于大城市周邊的衛星城和城市群。
再者,城市化其經濟性質城市配套上會都與城鎮化有些區別。城市化偏重于城市商業中心這樣的概念,城鎮化在基礎設施和配套方面沒有城市化那么高,如果一定要區分我認為就是這個區別。
最后,十八大提出這個城鎮化的精髓是四化概念,即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城鎮化,這四化是有互動和關聯的。
具體到房地產關聯的方面就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如農民征地補償的制度,土地流轉的方式,宅基地的自由流轉等,另一方面,城鎮化還涉及到公共服務是否能均等化,以2011年城鎮化率來說,戶籍人口只有35%,而常住人口為53%,這中間的流動人口是否可以享受到本地市民應有的教育、醫療以及其它配套服務,而這是新型城鎮化的重點問題。
一方面,過去三十年的城鎮化步子邁得有點大,因此出現了很多問題;另一方面,城鎮化也并不等于房地產,房地產在城鎮化的過程中應該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在新的形勢下,房地產開發商在經后產業園開發、旅游地產建設等方面應該改變一下思路,而不是按照以前的思路開發,開發商需要正確對待城鎮化。
中銀國際黃海勇:在長三角、珠三角這樣的一線城市,城市集約程度太高,導致發展過程中出現一些的問題,比如房價和收入不匹配,當房價過分上漲時,會積累一些民生和社會問題。
新型城鎮化的方向是非常好的,正是因為管理層看到了這一點,在推出新型城鎮化的時候是理性的,同時闡釋了金融創新,還提出來“打擊投資性房地產投資行為”。
主持人:《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已對外發布,您對這個規劃如何解讀?
劉國宏:我認為新型城鎮化規劃有幾個亮點。規劃的指導思想提到了從土地的城鎮化轉向人口的城鎮化,避免了過去強調土地資源的開發建設,沒有考慮土地所承載的具有創新能力的人群的需求的問題。
規劃還特別提到了要以城市群作為支撐,這也是不同于以往的一個提法,實際上是對以前的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的反思,同時對以前城市化階段產生的效果還是有認可的部分。因此,新型城鎮化應該主要往原來已經形成集聚的城市群進行再布局,提高區域的經濟密度,進一步提升規模效應。從提升國家的經濟競爭力來看,這都是有意義的。當然規劃和實際的實施還是有距離的,我們對它充滿了期望,也預示著接下來執行層需要更加努力地做好。
談到資源,從投資的角度來說要追求利潤,從社會配置的角度來說要更有效率,那么投到什么地方更有效率?我覺得,對于城市化、城鎮化的理解,應該由市場說了算。這次國家提的規劃里面提到了城市群,
從個人角度,我覺得規劃在促進資本、人口流動方面還是有所欠缺的。比如說,它仍然使用了一些控制的字眼,我覺得應該更多的強調從控制轉向保障公平、轉向怎樣在各個區域里邊公共資源的公平配置,從而調整人口,解決人口集聚過多產生的問題,而不是采取行政手段。
規劃只到2020年,是短期型的規劃,從長期來看,還是要更多的通過保障公平的方式,通過市場化的手段來促進和推動城鎮化建設,我覺得這個才是正途。
主持人:當然,我們更加關注新型城鎮化帶給房地產行業的影響。那么,隨著新型城鎮化的推進,對房地產行業市場有著怎樣的影響?
王飛:新型城鎮化給房地產行業帶來的機遇,首先是區域方面的。目前的城鎮化東部是高于中西部地區的,規劃出來之后,里面提到一億人要就近城鎮化,這對未來中西部地區有一些利好。
第二,對于中小的微型城市群來說也是存在很大利好的。大家也看到了舊的城鎮化帶來的一些諸如“空城”“鬼城”的問題,因為相關的商業、公路等基礎建設沒有跟上。現在的規劃以中大城市、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為依托,在周邊建設微型城市,相對應會有城際間的軌道、相關的商業配套跟上,這種城市群對于微型城市來說也是存在很多利好的。
第三,規劃提到了老城區的改造問題,在深圳的土地供應基本上是以舊改或城市更新為主,去年三分之二的土地供應來自于城市更新,未來這個比重還會繼續加大,這也是一個新的趨勢。 第四,對于包括旅游地產在內的這些產業地產也是存在機遇的,未來產業園的建設力度會加大的。
主持人:在新型城鎮化發展的背景下,房企投融資體制將如何改革。
黃海勇:走到今天,我們看到的了一些空城,這是不是給我們敲了一個警鐘,“攤大餅”式的城鎮化不能再走下去了。從資本市場我們看到,十年調控,房價漲了十倍,但是房地產的股票跌了十年,這是違背經濟學的投資邏輯的。
所以,新型城鎮化一定不能等同于房地產化,在實施的過程中如何避免“攤大餅”式的發展,這是需要考量的,比如在農村人口進行城市化轉移的過程中,如何提高消費水平、勞動生產率等等。
主持人:據了解,萬科、保利、恒大等房企已經開始在幾大城市群中悄然布局土地儲備,請問您對此怎么看?您所在的企業有什么具體的舉動?
王飛:大家都看到去年整個土地市場的熱度,其實從標桿房企很多從三四線重新回歸到一二線城市,包括從去年下半年以來拿地的熱情,很多城市溢價率能翻幾倍。一個方面,開發商對于這種規劃、利好的敏感度是很高的,另外一方面也跟土地財政的事實其實是分不開的。很多城市從11年到12年,整個房地產市場其實是有一段低迷期的,12年第二季度開始有一些回溫,很多地方政府他的財政其實是面臨很大問題的,到了12年下半年,土地市場熱起來其實也跟地方政府自己拼命推地是有很大關系的,所以不是說房企悄然進行土地儲備,而是跟地方政府的關系非常大。
主持人:兩會期間,住建部提出:今年房地產政策“雙向”調控。大部分觀點認為,所謂的“雙向”就是差異化。在座的各位是否同意,能否結合深圳樓市的現況談談您的理解?對深圳房地產形勢有哪些影響?
王飛:我理解的雙向調控應該從幾個方面去說,第一,城市不同,一二線城市和三四線城市樓市現狀是完全不一樣。三線城市樓市供應過剩,去化周期之前爆出南京去化要18個月,而深圳是不同的,一線城市去化周期目前還處于一個相對穩定的時間段,深圳要9個月左右,其他一線城市也是一個比較合理的水平,這是雙向調控差異化的其一;其二在于,對于需求和供應它也是雙向調控的。之前的行政政策,都是限購、限貸,都是從需求的方向來講。政府說促供應也是一直在提,比如保障房的供應,要求兩條腿走路。真正離能達到加大供應的結果還是有一定的差距,我理解,今年政府在供應方面應該會有一些動作出來。第三,剛需市場和高端市場,即自住和投資,也是調控差異化的問題。剛需實際上出現房貸緊張,從政府意圖來說要保障剛需,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對于投資需求,其實政府從很多年前就打算打擊投資、投機行為。深圳來說從09、10年的30%以上的高投資占比,經過10年、11年調控,投資客從監測的數據來看有大筆的回落。去年和今年的水平就是百分之十幾道二十以內的幅度,這也是調控的一個重要方向。 |